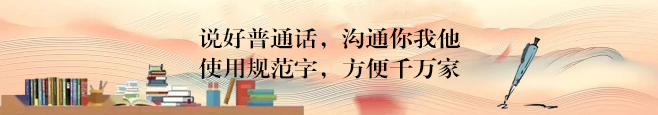农场往事
阿航
随着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海南农垦终于到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时候了。农场的往事不由得点点滴滴渗进记忆中来,以前总觉得象流水帐一样平淡无奇,甚至有点无聊乏味。如今细细嚼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此,把这些往事从回忆中采撷下来,算是一种留恋吧。
兵团生活
海南农垦起源于部队建制,因此而保留了许多部队的痕迹。我生活的农场在上世纪70年代就属于第三师第八团。场部叫团部,生产队叫连队,我所在的连队就叫二十二连。所谓的连队,老老少少应该有二、三百来号人,来自全国各地、南腔北调都有,就这么挨家挨户的住在由公家统一修建的砖瓦房里,一排排整齐的罗列着。连队正中央挺立着一株已有上百年的酸豆树,枝繁叶茂,树干粗壮,要好几个人才能环抱,这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每年没等树上的酸豆长大成熟,早被我们爬上去摘下来,然后用盐和辣椒拌着吃了,又酸又辣又咸,现在回味起来还直咽口水。
最难忘的就是傍晚时分,随着家家户户房顶上的炊烟渐渐散去,忙碌了一天的家庭主妇端出来虽不太丰盛、却也十分可口的饭菜。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吃晚饭都习惯摆在门外。一排房子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同时开饭,场面十分壮观。谁家饭菜的优劣都一目了然,因此各家主妇暗自较劲,尽显神勇。有两广的,有闽南的,有湘楚的,甚至还有山东河南的,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是什么风味的香气。
孩子们被饭菜的香味吸引,纷纷停止玩耍围向各家的餐桌。也有个别顽童耍到兴起而忘了吃饭的,这时就会传来母亲不耐烦甚至有些粗鲁的大吼:“叫回来吃饭不回来吃饭,死哪去了?整天就知道玩,你这个粪箕,没用的东西,等我挖个洞埋了你!”说着还顺手捡起一根棍子。这时家人早已围坐在餐桌边了,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永远不忘了保持镇定,边吃边说:“叫什么叫,饿了自己会回来。有功者留饭不留菜,无功者饭菜不留。”
吃饭的时间其实也是邻里相互交流沟通的时间。大人们边吃边聊,爱喝两杯的则邀请对方坐过自家的餐桌,而被邀请的总不忘端一盘自家的好菜过来,就这么几个大人可以直喝到天完全暗下去才罢了。此时的孩子们也瞅准机会,端着饭碗“跑场”,等着别人家赏赐的好菜。这种行为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会受自家父母制止的。
天晚了,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灯。饭后,男人们就聚在走廊继续喝茶聊天。女人们的劳累却并没有结束,她们还得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和安排孩子们洗澡,然后再为全家人洗衣服,直到夜深人散时才能休息。
农场的一天就在这和谐温馨的夜色中落下了帷幕。
大会战
海南农垦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那时期的农场经常要开荒种胶,称之为“大会战”。每到大会战时,各连队的青壮年男劳力就会被抽调往还未开垦的边远山头,集中在一起开荒垦殖。男人们吃住都在工地上,一干往往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长达一两个月。家里只留妇女照看小孩和老人,我们只有在随母亲送换洗的衣服时才能到工地上感受感受大会战的氛围。
到了工地现场,只见连绵几座山头旌旗招展,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革命歌曲,人们热火朝天、挥汗如雨,场面十分壮观。各连队都分配有各自的山头高地,展开激烈的劳动竞赛,一座座荒山就在人们的竞赛中变成了勃勃生机的橡胶园。
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大人们休息的时候了——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愿意跑那么远的路的目的了吧。在紧张的劳动间隙,为了补充体力,工地上的临时伙房会提供各种美味的工作餐,有包子、馒头、肉粥等等,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就来抢占瓜分大人们的食物。这时,伙房的师傅们总是有意多打点给我们,直到我们把肚子吃到鼓鼓的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
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大会战硝烟早已散尽,只是父辈们劳作的背影还历历在目,眼前青山上那郁郁葱葱的橡胶林似乎在为他们默默地作证。
狗叔
前两年我回农场时,听母亲说狗叔去世了,死于肝癌,还不到六十岁。回想狗叔的一生,不免心中怅然。
狗叔是我家的邻居,60年代末随姐姐来海南的,当时只有十六岁吧。由于个子瘦小,又无一技之长,狗叔快三十了才由姐姐介绍,从罗定家乡娶了比他小七、八岁的狗婶。因此,狗婶一直看不起他,两人经常吵架。特别是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后,狗婶凭着自己的胆大心细,和别人在外跑了点小生意后,逐渐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两人的婚姻就开始了危机。最伤狗叔自尊心的就是,狗婶经常拿整打的钞票在他面前显摆,还说“俾你睇,唔俾你使”——粤语:给你看,不给你用。为此,左邻右舍经常拿这句话取笑狗叔。狗叔从此更是萎靡不振,终日借酒浇愁,酒后不是胡言乱语,就是东倒西歪,也就更成了人们的笑料。
终于,狗婶再也无法忍受狗叔的种种不作为了,提出了离婚,带着两个孩子回广东了。狗叔从此一个人孤独潦倒,哪家有酒就往哪家去,就这么混日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应该是在五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听说他的儿子医学院毕业后,在广东茂名找到了一份好差事,特意祝贺他:“狗叔,你好命,强仔(狗叔儿子的小名)现在发达了,以后你就可以跟着他享福了。”
狗叔却说“哼!发,烂脚就会发。”虽说狗叔表现出一脸的不屑,但随后却滔滔不绝地和我聊起儿子的近况,脸上还似乎泛出一丝红光。
听母亲说,狗叔去世前的半个月,狗婶和强仔还从广东赶回来照顾他,直到他去世并料理完后事。
狗叔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从青春少年直到黯然离世,似乎承载了农场往日的荣耀和曾经的迷茫,也寄托了多少农垦人的憧憬和期待。
冼老师
我在小学时有两位姓冼的老师,这两位老师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农场的知青。第一位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广州知青。在我印象中,她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师,几乎没有严厉批评过我们。而且写得一手好板书,可惜她只教了我一个学期,我经常会想起她。
另一位冼老师是位广西梧州来的知青,她是我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主任。冼老师对我们非常严格,做事十分利索,很有责任心。当时我是班上个子最小的男生之一,却上课总爱搞“小动作”,常惹女孩子生气。也许是我的语文成绩较好的缘故吧,冼老师又是教语文的,因此她很喜欢我,经常让我在课堂上范读作文,也总能宽容我的缺点,但是这逐渐也助长了我那骄傲的心理。
有一次改选班干部时,我落选了。冼老师看出了我的沮丧和懊恼,就提意让我担任小组长。没想到却被我当场回绝了,当时同学们都惊呆了,冼老师也愣了一下,但她没有坚持,也没有责备我。我不记得当天是怎么上完冼老师的语文课的了。
从那以后,我的成绩很不稳定,这很快引起了冼老师的警觉,但是她不露声色。直到一天上午放学后,我和同学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看到冼老师远远地跟在后边。当时我也没多在意,心想,也许老师有事情要外出办理吧。直到冼老师跟着我走进我们连队时,我才紧张起来——完了,冼老师准是到家里“告状”来了!
在我父母的眼里,老师的话简直就是“金科玉律”,冼老师的到来让他们十分高兴,而我却在一边可怜的直冒冷汗——看来吃一顿“面条”是免不了的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恨起老师来。可能当时大脑里早已是一片空白,大人们谈些什么,现在已是一点也不记得了。然而意外的是,那天我竟然没挨打!
这次家访的后续发展自然也很明了了,我更喜欢上冼老师的课了,成绩也稳步提高了。只是多年后父亲每每提到冼老师时总是一再嘱咐我:“你可别忘了冼老师呀,哪有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跑了近两公里来家访的!”
如今,冼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了,身体一直不太好,我回农场时也尽量抽空去看她。两位冼老师和当年的许多知青一样,正值豆蔻年华,为了海南的教育事业来到农场,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农垦职工的子女们。今天,我也成了一名教师,我会以她们为榜样,做一盏知识的明灯,去点亮每一颗求知的心。
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50年代末到农场的退伍兵。也许是当过兵的原因吧,父亲的性格非常暴躁,象那个年代的许多父亲一样,是家里绝对的“君主”,孩子们都非常怕他,没少挨他打。不过父亲也偶尔有其耐心和温情的一面,特别是在向我们讲述他的“传奇经历”时,可以说是津津乐道而不厌其烦,我们兄妹三人就是伴随着父亲的故事渐渐成长的。
其实所谓的传奇就是父亲的奋斗史。父亲小时非常淘气顽皮,无心上学,只读了三年小学就缀学在家了。但是父亲自小就孔武有力,经常和别家的小孩打架。于是邻家不断告上门来,为此父亲总少不了挨我大伯一顿好打——以前乡下的家庭孩子多,大伯父比父亲年长十几岁,甚至还当过国民党时期的村长,奶奶只好疲于应付。到了父亲14岁时,奶奶不得不忍痛把父亲送出去自谋生路。于是还在年少时期的父亲就随其他年长的叔伯来到广东徐闻种甘蔗和剑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7岁时,父亲到湛江当了兵,三年后退伍,先后到过莺歌海盐场铲盐,八所铁路局铲煤,最后到了定安县中瑞农场种橡胶。1960年,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党中央号召退伍军人重返部队准备打老蒋,父亲一点都没犹豫就报了名,开始了第二次从军的历程。无奈时运不济,第二次当兵还不到一年,老蒋不敢来了,重返部队的老兵不得不再次放下枪杆退伍,父亲再次选择了回海南,这次被分配到了三师八团,也就是现在的南田农场,一直到退休、离世。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也只是一名普通退伍兵,并没有做出什么传奇的业绩。只是在当年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却是我们仰慕的英雄。当时我问父亲重返部队时不怕打仗死人吗?父亲笑笑说:“有什么好怕的,死了就死了,不死还能安排个好工作”——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极其普通农垦老工人。
往事如烟,留给我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淡淡的哀愁,甚至最终会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但农垦人的精神将继续激励着我,驱使着我踏着父辈们的足迹,眺望着他们的背影,一路前行。